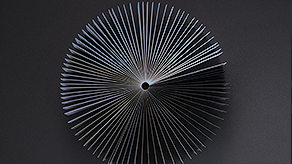中企海外矿业投资面临的社会许可风险
中企海外矿业投资面临的社会许可风险
近年来,随着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各国鼓励、推动绿色矿产投资的浪潮方兴未艾,这既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监管要求和投资风险。其中,要求矿业投资者、经营者与当地社区居民和谐共存,已成为各国特别是拉美等传统资源国对绿色矿产投资监管的必然要求,“社会许可”的概念也随之应运而生。
一、社会许可的概念及背景
“社会许可经营”或“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源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矿业开发导致的当地社会冲突,其核心含义是指矿业项目除需获得法律许可外,还需取得利益相关者对采矿开发的持续性接受和认同。[1]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项目的人,他们可能包括当地居民和意见领袖、有组织的团体(如政党或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
有别于传统的法律许可,社会许可不是一个发展完善的法律概念,不仅国际法理论界对其概念内涵多有争议,各国国内实践对社会许可的要求也较为宽泛模糊,缺乏文件指引,这给矿业投资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因社会许可问题导致项目开发停滞、投资受损甚至投资者求偿受阻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亦不乏中国投资者的身影。自2014年7月,中国五矿资源牵头组成的联合体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以来,该项目因当地社区堵路、工人罢工导致生产中断的事件屡屡发生,[2]类似封锁道路的事件在2025年7月又再度上演。[3]2018年5月起,中国庄胜黄金投资的厄瓜多尔金银矿开采项目遭遇不明身份人士闯入占据,与此同时当地法院应部分个人及原住民组织申请,以禁止在受保护的自然区域采矿为由作出暂停开采决定,庄胜黄金已根据中国厄瓜多尔BIT针对厄瓜多尔政府提起投资仲裁,2025年6月仲裁庭以多数意见维持了对该案征收争议的管辖权,目前实体审理仍在进行中。[4]
鉴于此,下文将从国际投资仲裁案例的角度,系统梳理社会许可对矿业投资者的可能影响及风险,为中企海外矿业投资的风险防控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社会许可对矿业投资的可能影响
(一)因当地社区反对导致东道国终止项目或撤销许可
违反社会许可对矿业投资者的最直接影响,是可能导致东道国剥夺投资者从事矿业活动的相关许可。实践中,该等风险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1)当地社区居民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诉诸国内诉讼挑战投资项目的合法性,并获得东道国国内法院支持,判决中止或撤销投资项目已获得的法律许可;(2)当地社区对项目的强烈反对引发东道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为平息社会动乱,东道国政府可能采取拒绝授予、撤销项目法律许可,或施加额外要求等不利于外资的干预措施。
就东道国采取的上述措施,尽管投资者理论上仍可诉诸东道国国内的行政或诉讼程序,但一般成功率不高,且由于与当地社区关系恶化,导致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活动可能举步维艰。因此,投资者可考虑国际法下的救济途径,即提起投资仲裁,主张东道国的行为构成征收或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并要求东道国给予损害赔偿。诉诸投资仲裁要付出时间和经济成本,但至少可以与东道国就争议事件进行直接沟通。
在此类案件中,仲裁庭关注的焦点问题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1)投资项目遭受社会反对的程度,以及投资者针对社区关系所采取行为的合理性;(2)东道国撤销许可前的行为是否为投资者创设了合理期待,以及东道国撤销许可的程序本身是否符合正当程序。
若投资项目遭受当地社区严重反对,而投资者怠于修复社区关系,甚至采取较为激烈的手段对抗当地反对力量,则可能排除东道国行为的非法性。如在South American Silver v. Bolivia案[5]中,仲裁庭认为,投资者SAS在与当地社区的互动中存在严重不足,其“社区关系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缺陷,且未能采纳咨询公司建议的改进措施,反而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对抗反对项目的社区领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玻利维亚政府撤销SAS开采权的行为是为了应对社会动荡和保护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符合公共目的的要求,不构成非法征收。
若投资者虽在社区外联方面存在不足,但未上升至激烈对抗的严重程度,而东道国政府既未向投资者披露当地社区态度,也未建立必要的投资规制或沟通机制,则通常认定投资者的行为已满足东道国的社会许可要求。此时,东道国撤销或拒绝授予许可的行为可能构成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损害,进而违反公平公正待遇要求。如在Crystallex v. Venezuela案[6]中,仲裁庭认为委内瑞拉政府此前的审批行为给投资者创设了环境许可证可顺利发放的合理期待,而此后委内瑞拉环境部突然以项目会对矿区周边环境及土著社区造成不利影响为由拒绝发放环境许可证,损害该合理期待,且上述理由此前从未与投资者沟通并倾听其回应,行政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构成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情形。
(二)因当地社区的暴力行动导致投资者丧失对矿区的控制权
除因当地社区反对导致东道国直接撤销矿业许可外,违反社会许可的另一现实风险是,投资项目可能招致当地社区的激烈反对甚至暴力对抗,阻碍甚至占据相应矿区,影响矿区正常经营活动,危及矿区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坏的结果是,投资者尽管理论上仍享有相应矿区的法律权利,但事实上已完全丧失对相应矿区的实际控制和经营管理能力。
就上述情况,投资者可考虑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协调和救济,但因此类对抗事件涉及当地利益,较为敏感,通常协调难度大,且相关资源国政府(特别是拉美国家)往往缺乏采取有效措施的行政能力和相应资源。在此情况下,投资者仍可考虑将东道国诉诸投资仲裁,主张东道国的行为构成间接征收、违反充分保护和安全义务或公平公正待遇,要求东道国提供损害赔偿,但因此类案件往往缺少东道国违反条约义务的积极行为(如直接撤销许可),投资者需证明当地社区的行为或其导致的结果可归责于国家,举证难度更大。
在2025年6月30日最新作出的Lupaka v. Peru案[7]裁决书中,仲裁庭认定秘鲁当地社区的行为可归责于秘鲁国家,最终裁定秘鲁需赔偿Lupaka 4,040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所有法律费用和开支。该案仲裁庭说理可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该案涉及加拿大矿业公司Lupaka投资的秘鲁金矿项目,尽管投资者与当地两个农村社区保持友好关系,但另外一个农村社区强烈反对该项目,采取了临时占领矿山、永久封锁矿山通道等行为,导致Lupaka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最终失去了对矿山的控制。2020年,Lupaka根据加拿大-秘鲁自由贸易协定(FTA)向ICSID(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起仲裁,索赔超过4,000万美元。在论证当地农村社区的行为可归责于秘鲁国家时,仲裁庭的具体理由包括:(1)农村社区可被视为国家机关,原因是根据秘鲁宪法和国内法律,农村社区在经济、行政、安全(通过社区巡逻队)和司法领域被赋予了重要的国家职能;(2)农村社区封锁和占领矿山的行为并非个别成员的私人行为,而是社区及其领导层的集体决策,即使该等行为超出社区的法定权限,但秘鲁仍应对这些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负责;(3)秘鲁政府在应对社区行为时存在不作为,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投资,也未能对社区的非法行为进行干预,最终导致Lupaka失去对矿山的控制,构成间接征收,违反了全面保护和安全义务及公平公正待遇标准。
(三)因缺乏社会许可导致投资者的索赔主张无法得到全额赔付
除项目开发受阻、法律许可被东道国撤销,缺乏社会许可对投资者的另一风险是,其在投资仲裁中主张的索赔金额可能无法得到仲裁庭的全额支持。
已有仲裁实践表明,仲裁庭确实会综合考虑投资者的行为并调整赔偿数额。一种情况下,仲裁庭会基于投资者及其项目遭受社区反对的事实,驳回投资者的预期利润损失诉请。例如Bear Creek v. Peru案[8]中,仲裁庭指出,由于涉案项目几乎没有希望获得必要的社会许可,项目的投机性和不确定性太大,无法采用考虑项目预期盈利的贴现现金流法(DCF)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因此应参照投资者的实际投资额来计算。另一种情况下,投资者未能妥善处理社区关系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促成过错,根据其对损害的贡献程度相应地减少赔偿数额。例如Copper Mesa v. Ecuador[9]案中,投资者面对东道国当地居民的挑衅,通过招募和使用武装人员,向平民开枪、喷射催泪喷雾等暴力行为恶化社区关系,被认定应对其自身损失负有30%的责任,损害赔偿数额也相应减少30%。
除仲裁实践外,已有国家将“投资者缺乏社会许可”认定为促成过失写入投资条约,如《印度2015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26.3条[10]明确要求仲裁庭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应考虑投资者“对当地社区造成的任何尚未补救的损害或破坏”等减轻损害的事由,并相应减少损害赔偿数额。然而,目前还缺乏仲裁庭适用类似条约的案例,其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
(四)东道国以投资者违反社会许可为由对其提起反请求
投资者违反社会许可,理论上亦可能面临东道国以投资者污染环境、损害当地人权等为由提起的反请求,但此类投资仲裁案件较少。
在2016年Urbaser v. Argentina案[11]中,仲裁庭首次允许东道国对投资者的反诉,并主动援引除投资协定以外的法律渊源,包括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与1966年《经济、社会与文化人权国际公约》,认定投资者除享有被投资仲裁条约保护的权利外,亦有“不妨碍个人用水权”的国际法义务,但该案中阿根廷并未就反请求主张单独的损害赔偿数额。因此,此类问题仍有待于仲裁实践的检验。
三、社会许可对中企海外矿业投资的启示
在全球绿色矿产投资方兴未艾的宏观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资矿企选择走出国门、远赴海外投资,其在迎来难得机遇的情况下,也面临着资源国越发严苛的社会许可要求。尽管该等要求在许多国家仍未以法律形式明确固定下来,但社会许可的缺失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投资风险。
因此,为审慎管理海外矿业投资,尽量避免或减少社会许可风险对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建议中资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首先,在进行关键行业的投资前,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东道国针对该行业的特定立法,预先对该国该行业市场环境进行调查和综合研判,预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许可风险。特别是在收购时已经存续经营一段时间的项目,需全面考察其既往社会许可历史(包括当地社区对项目的支持程度、项目涉诉情况等),可考虑在相关投资协议中,要求相对方以陈述保证等形式就项目既往社会许可情况作出保证,并设置违约赔偿条款。
其次,投资者在对矿区进行开发和运营时,应基于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符合当地居民需求的措施,以获得土著居民和社区组织的支持,以此来缓解采矿运营可能引发的冲突。同时,可通过更好地支持区域发展和受采矿影响地区和居民的发展(如雇佣当地居民、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等)来维护“社会许可”,以保障矿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跨境矿业投资人的利益。
最后,在与当地社区发生争议甚至冲突时,建议投资者采取理性克制的应对手段,避免因为己方手段导致矛盾升级,可积极寻求东道国政府的介入和协调,尽量通过法律程序寻求争议解决。在当地投资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投资者应及时寻求国际法下的救济途径,包括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磋商、调解和/或诉诸投资仲裁机制,至少在短期内将其损失和诉求与东道国交涉,并最终通过法律程序实现诉求,保护海外投资的利益。
[注]
[1]Boutilier, R. and Thomson, I., The Social License: The story of the San Cristobal Mine, Routledge-Greenleaf, Abingdon, UK, 2018, pp. 41-42.
[2]界面新闻:“员工要求额外补偿,五矿资源旗下秘鲁铜矿发生罢工”,2023年11月29日,https://finance.sina.cn/2023-11-29/detail-imzwhxhp2139626.d.html.
[3]全国工商联一带一路信息服务平台:“秘鲁铜运输受到严重干扰”,2025年7月10日,https://ydyl.acfic.org.cn/ydyl/fxts/2025071001385257348/index.html.
[4]Junefield Gold v. Republic of Ecuador, PCA Case No. 2023-35, Partial Award on Jurisdiction dated 2 June 2025.
[5]South American Silver Limite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Award dated 22 November 2018.
[6]Crystalle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AF)/11/2, Award dated 4 April 2016.
[7]Lupaka Gold Corp. v. Republic of Peru, ICSID Case No. ARB/20/46, Final Award dated 30 June 2025.
[8]Bear Creek Mining Corporation v. Republic of Peru, ICSID Case No. ARB/14/21, Award dated 30 November 2017.
[9]Copper Mesa Mining Corporation v. Republic of Ecuador, PCA No. 2012-2, Award dated 15 March 2016.
[10]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 Model Text for the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3560/download.
[11]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26, Award dated 8 December 2016.